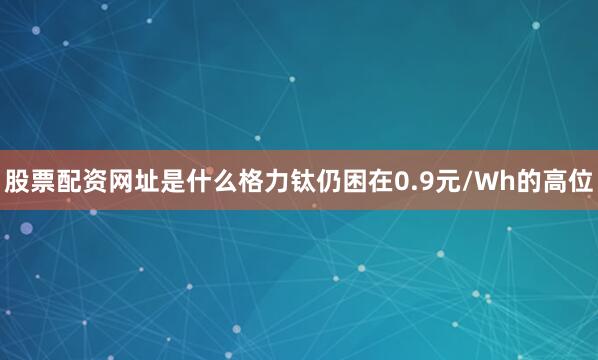
2025年6月,格力钛新能源18.06亿元股权被封存至2028年。背后,是格力电器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持续8年的战略豪赌,正面临债务危机、技术路线争议与市场溃败的三重拷问。董明珠的“造车梦”,正成为检验企业家战略定力与市场规律的典型样本。

一、技术路线之争:钛酸锂的“安全执念”与市场溃败
格力钛的核心技术——钛酸锂电池,曾被董明珠视为“颠覆行业”的利器。这种电池能在零下50度环境正常工作,循环寿命达3万次,且从未发生火灾事故。董明珠在2025年4月股东大会上强调:“技术路径选择肯定没错,产品的第一要素就是安全。”然而,市场用脚投票给出了残酷答案:格力钛面包车续航仅230公里,满载后不足200公里,售价从15.8万元暴跌至5万元仍滞销;客车销量从2016年全国第三跌至行业十名开外,市场份额不足3%。
技术参数的硬伤直指要害:钛酸锂电池能量密度仅为58-110Wh/kg,而主流磷酸铁锂电池已达240Wh/kg。这意味着同等电量下,格力钛车辆需多背负数倍重量,直接导致商用客户运营成本激增。更致命的是成本劣势——钛酸锂制造成本是磷酸铁锂的3倍,当比亚迪、宁德时代通过规模化生产将电池成本压至0.3元/Wh时,格力钛仍困在0.9元/Wh的高位。2024年中报显示,格力钛营收19.87亿元,亏损却高达19亿元,相当于每卖一辆车亏损超60万元。
二、战略误判:从“全产业链掌控”到“资产黑洞”
董明珠的造车路径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。2016年,她力排众议以个人名义投资珠海银隆,后通过格力电器司法拍卖、股权收购等方式累计投入超50亿元。这种“个人信用背书+上市公司接盘”的模式,在格力钛深陷财务困境后暴露出致命缺陷:截至2024年底,格力钛负债247.86亿元,资产负债率逼近100%,格力电器不得不对其28.44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。
更严峻的是治理结构混乱。原银隆创始人魏银仓2018年因侵占公司资产超10亿元被引渡回国,暴露出董明珠团队在并购尽调中的疏漏。而格力钛目前面临的17起法律纠纷中,15起为买卖合同纠纷,供应商付款延迟、客户交付违约等问题频发,折射出其运营体系的系统性崩溃。
三、转型突围:从“全面出击”到“特种车辆”收缩
面对败局,董明珠在2025年6月被迫调整战略:格力钛将彻底退出家用车市场,聚焦环卫车、重卡、公交车等工程车辆领域。这一转向暗含两层逻辑:其一,工程车辆对续航敏感度较低,更看重电池寿命与安全性,与钛酸锂特性部分匹配;其二,通过放弃乘用车红海市场,减少与比亚迪、特斯拉等巨头的直接竞争。
同步进行的还有组织架构切割。2024年10月,格力成立上海格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,注册资本2000万元,经营范围限定为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。这种“轻资产+技术输出”模式,既保留了汽车产业链参与度,又避免重蹈整车制造的巨额投入覆辙。格力电器2024年财报中,格力钛相关业务描述被医美产品板块替代,标志着造车战略在集团层面的实质性边缘化。
四、董明珠的“最后一战”:品质执念与时代变局的碰撞
在6月郑州董明珠健康家开业仪式上,董明珠再次强调:“靠流量忽悠消费者的做法难长久,格力空调用10年不坏才是真本事。”这种对品质的执念,在空调主业上确实构筑了护城河——格力2024年研发投入占比达4.67%,新增专利授权1335项,主导制定的两项制冷压缩机国际标准填补行业空白。
但新能源汽车的败局,暴露出传统制造思维在智能电动时代的局限性。当小米、华为等科技企业通过生态链整合、软件定义汽车快速崛起时,格力钛仍困在“电池安全-续航短板-成本高企”的死循环中。董明珠的“不赶时髦、不吹牛”哲学,在需要颠覆性创新的赛道上,可能成为束缚手脚的枷锁。
五、格力困局背后的制造业转型启示
格力钛的案例,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一面镜子:在技术路线选择上,安全性能与市场需求的平衡至关重要;在战略决策中,企业家个人意志与产业规律的契合度决定成败;在转型过程中,传统制造优势如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,仍是未解难题。
截至2025年6月,格力电器董事会提名71岁的董明珠连任三年,市场对其“再干三年”的期待与质疑并存。而格力钛的18.06亿元冻结股权,就像悬在格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——这既是董明珠造车梦的残影,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支付的学费。当潮水退去,方知谁在裸泳;当泡沫破灭,始见真正价值。格力的故事,远未到终章。
炒股软件排名前十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